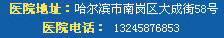再论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
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判例(-)
章剑生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行政法学理上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解释,与年之前相比并没有发展出新的学说;对“程序轻微违法”解释主要是通过整理判例列出若干情形,但未作类型化处理和一般化判断规则的提炼,以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作为认定“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方法,实务中则更具有可操作性。结合过去0年最高法院公布的判例,我们可以发现“违反法定程序”作为司法审查标准未能发展出更为精细化、多元化的判断标准;在没有法定程序的情况下,法院仍然采用“正当程序原则”的司法审查标准,但它不断地扩大其适用的行政领域范围。年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后,未见最高法院公布因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作出确认违法判决的判例,这种状况可能会影响法院确认违法判决的正确适用。
关键词法定程序正当程序程序轻微违法行政诉讼司法审查
一、引言
年我在《法学研究》第2期发表了题为《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一文,该文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发布的相关判例,结合行政法学既有的学说,对《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第3目“违反法定程序”这一司法审查标准当如何解释这一问题,借助“个案—规范”的方法论框架,分析法院判例中的裁判理由,进而得出如下两个结论:()认定标准。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行政程序为“法定程序”;在没有“法定程序”情形时,法院可以引入正当程序原则辅助判断之;(2)判决方式。在认定被诉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之后,法院首先考虑“是否有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之因素,并视具体情况不同选择撤销判决、确认判决或者驳回诉讼请求判决。
此文发表之后,我计划基于最高法院同一主题上的持续性判例,在法政策调适过程中观察其裁判立场的变迁,在0年之后写一篇“再论”,以延伸自己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在过去的0年(-)中,关于“行政程序违法”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但行政法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相关研究或多或少还是有所推进的。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第70条在保留《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第3目“违反法定程序”之外,在第74条第款第2项中又添加了一项新的规定,即“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权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法院可以判决确认其违法,但不撤销该行政行为。在这0年中,最高法院公布判例的方式从原来比较单一的“公报案例”[],到今天“指导性案例”和“行政审判案例”[2]并存,判例的数量有了较快的增长,其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升,这都为我们今天研究最高法院如何解释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和适用何种裁判方式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
本文的写作思路是,在解释相关法规范和整理过去0年中行政法学界对“违反法定程序”研究成果基础上,透过最高法院公布的相关判例(-),着重讨论如下三个问题:()认定行政程序违法是否需要基于行政程序的分类基础?(2)行政程序违法的裁判方式如何适用?(3)当以何种价值取向引令法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本文的写作意义是,通过阶段性的、同一研究视角的方法,揭示最高法院对“违反法定程序”司法审查态度的变动轨迹,一方面可以回应《行政诉讼法》立法、修法的旨意,另一方面也为地方各级法院的司法审查提供一种规范性的指引,尽可能地接近“类案类判”这一统一法律适用的目的。
二、法律规范分析与学说发展
(一)法律规范分析
《行政诉讼法》()除了在第70条保留了“违反法定程序”之外,它又在该法第74条第款规定的确认违法判决要件中,添加了“程序轻微违法”和“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两个新概念。对于“违反法定程序”,在法解释学上我们可以从“程序”、“法定程序”和“违反法定程序”三个层次来作文义解释,阐明其法意。对此,我在《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一文中已有充分论述,本文沿用这一解释结论,不再重述。这里重点分析《行政诉讼法》()添加的“程序轻微违法”和“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两个新概念,并从体系解释上厘清与“违反法定程序”之间的关系。
.程序轻微违法。作为确认违法判决要件之一的“程序轻微违法”,从法解释学上看它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在这个法概念中,本文认为重点是对“轻微”当作如何解释。()就文义解释而言,“轻微”有“不重要”、“程度轻”之意,相对于“轻微”情形的另一端则是“严重”。[3]由此可知,在“轻微→严重”这一语言分析框架中,如同光谱的“亮→暗”那样,但在哪一个刻度上划出“严重”与“轻微”分界线,抽象的、可操作性标准可能是不存在的。较为妥当的方法是回到立法论上,在“法制定—法裁判”的关联框架中,由立法者授权法官在个案中考量各种因素之后酌定。(2)就体系解释而言,这里要处理与《行政诉讼法》()第70条之间的逻辑关系,其解释结果不致于在行政诉讼法体系内产生紧张关系。对该法第70条中的“违反法定程序”,应当解释为行政行为所有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该法第74条第款中的“程序轻微违法”也在其中。或许有人会持有异议:在这样的体系解释之下,前者适用撤销判决,后者则适用确认违法判决,岂不矛盾哉?非也。因为,在行政诉讼裁判方法的逻辑体系中,确认违法判决本身就是撤销判决的一个“补充判决”,它的法构造是,本应适用撤销判决情形+法律特别规定=确认违法判决。进而言之,依照《行政诉讼法》()第70条规定,对所有“违反法定程序”的被诉行政行为,法院都可以适用撤销判决,但若有该法第74条第款特别规定情形之一的,裁判方式就要改撤销判决为确认违法判决。可见“程序轻微违法”属于“违反法定程序”情形之一,两者不非并列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于《行政诉讼法》第70条正确的理解应当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应当一律撤销,但行政行为属于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判决撤销,而是判决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4]本文认为,这一观点只有在以“违反法定程序”为上位概念,且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和“程序轻微违法”两分法之下才能成立。因为,在逻辑上还存在“中度程序违法”的情形,更何况,在法规范上还有可能推导出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产生了实际影响的情形。此时,法院当作何种判决,这一观点是难以给出妥当性答案的。(3)程序轻微违法与程序轻微瑕疵。在《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中,曾有“行政行为程序轻微瑕疵且能够补正的,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规定,但在立法审议过程中,“有的常委委员建议对‘行政行为程序轻微瑕疵’中‘轻微’作出界定,有的同志认为瑕疵本身就是轻微违法的含义,建议删去‘轻微’”。[5]因此,《行政诉讼法》()最终未采用“程序轻微瑕疵”这一概念。考虑到实务中一些法院使用“瑕疵”,有“合法不合理”或者规避“违法”之意,[6]《行政诉讼法》()最终未采用“程序轻微瑕疵”应该说也是妥当的。
2.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此为确认违法判决适用要件之二,同样包含了几个需要解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实际影响”。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在行政诉讼法中“实际影响”最早是作为确定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受案范围)的标准,出现在年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之中。[7]依照最高法院的解释,它“主要是指还没有成立的行政行为以及还在行政机关内部运作的行为等。”因为,“如果某一行为没有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提起行政诉讼就没的实际意义。”[8]年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解释”)第条第2款第0项保留了《若干解释》这一规定。依照体系解释规则,作为确认违法判决适用要件中的“实际影响”,若没有特别规定,两者应当作同一解释。若此,那么凡是有《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款第2项情形的,法院当以被诉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但是,这样的结论显然与《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款第2项立法要旨不合。对于这一点,立法者显然并没有意识到。(2)原告的义务。本要件中,程序轻微违法仅限于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那么,若对原告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是否不适用确认违法判决呢?查阅迄今为止公开的有关行政诉讼立法资料,我们未见立法机关就这个问题所作出的解释。最高法院在《行诉解释》中确定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时,它是包括原告“义务”的。[9]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断,《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款第2项的规定可能是一种立法疏漏。本文认为,基于权利与义务同等重要性,此处应当作目的性扩张解释,将原告的义务也包括其中,才能达成法规范体系上的逻辑自洽。
最高法院《行诉解释》第96条将“原告权利”改为“重要程序性权利”,把“实际影响”改为“实质损害”,前者有收缩确认违法判决适用范围之嫌,后者有消除与《行诉解释》第条第2款第0项“实际影响”之间紧张关系之意。在《行诉解释》法律框架之下,“程序轻微违法”=若干情形(处理期限轻微违法;通知、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其他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
(二)学说发展
本文所涉及的学说发展,主要有两个面向,一个是《行政诉讼法》()中的“违反法定程序”,另一个是《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款第2项的“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对于前一个问题,我在《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一文中有过系统的整理,故本文重点是讨论年之后学理上对该问题是否有推进性的研究成果以及对此作相关评述;对于后一个问题,因它是《行政诉讼法》()之后产生的新问题,故本文重点是对该既有研究成果的整理与评述。
.违反法定程序。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学理研究,这十年中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违反法定程序”中“法”范围的划定上。在《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一文中,我整理了当时行政法学界关于“法定程序”中“法”范围的研究成果,并归纳为“法律、法规规定说”、“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说”、“法律、法规、规章和宪法规定以及行政规定补充说”和“重要程序说”等四种学说。在这个十年中,这四种学说未有实质性的推进。但值得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zl/117.html